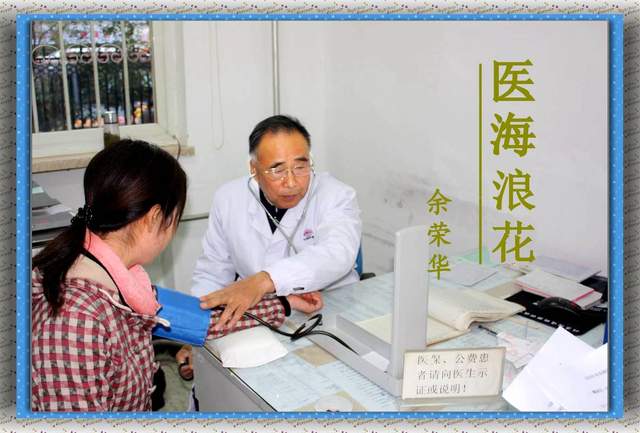
医 海 浪 花 (七)
余 荣 华
- 我当上了铁道兵
(一)白衣战士的欣喜
1965年8月15日,是毕业分配公布名单的日子,下午5点钟,我突然接到通知:马上到学生科开座谈会,到了学生科,已经有十多位同学就座了,有一位穿便衣的军人,非常爽朗地对我们讲,你们已经是铁道兵了,这时大家明白了,我们这几个人被分配到铁道兵了,我将是一名军人了,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,终于实现了去部队当兵去的理想,也就是说我将要穿上军装,成为一名白衣战士了。
离开家乡,途经南京,从南京坐上火车,又经过十八个小时,到了北京火车站。1965年8月28日,这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,我第一次来到北京,从北京火车站乘坐公共汽车,顺着长安街向西,在永定路附近,找到铁道兵8770部队,在干部科办理了报到手续,今天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,同时也意味着我学生时代的结束。在学校里读了十七年的书,学到了一些知识,今天终于走到社会上,成为一名铁道兵的医务工作者,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铁道兵全体官兵献出我的一切。这时候,豪情满怀,壮志凌云,心潮澎湃,在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,可是对谁说呢?只好写下片言只语,留在日记中,记录我的过往流年。
铁道兵8770部队,这是新组建的部队,负责修建北京地下铁道,从全国各地的大学和中专招来了很多的应届毕业生,总数将近百人,部队统称我们这些学生为学员。1965年9月2日下午,根据领导的安排,我们开始分配了,所有新学员都要分到部队基层去,我是被分在8779部队十一分队。先到团部机关,刘团长接见我们,讲了一些欢迎的话,干部股的闽登富干事又告诉我,要到十一分队报到,分队就在玉泉路西侧约一公里处,分队所属三个连队,都住在附近,部队的干部和战士,全部住在毛毡制成的帐篷里。来到十一分队,已是晚上六点钟了,一位个子很高的张营长接见了我,并告诉小通信员,到厨房做了鸡蛋面条,是用一个大面盆装的,这种面盆在我们家乡是用作洗脸的,现在部队用它盛饭菜,这还真是一件新鲜事。吃完晚饭,营长又告诉我,当晚要住到三连去,到了连队,藏连长更是热情又加,小通信员主动拿行李,安排床位、倒水、让座,十分亲热。在充满了新鲜、新奇、热情的气氛中,晚上八点钟左右,住到三连二班的帐篷里,帐篷里用木板搭起大连铺,班长睡在门口,我的铺位就靠在班长的右侧,躺在连队的帐篷里,久久不能入睡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突然又被一阵军号声惊醒了,原来是战士们已经起床了,他们在出早操,根据班长的安排,我例外地留在帐篷里,战士们在连部的小院子里,排成整齐的队形,一边跑步,一边喊着,一、二、三、四,接着又高唱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》:“背上了那个行装,扛起了那个枪,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,同志呀,你要问我到哪里去啊,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……”。歌声雄壮嘹亮。全连朝气蓬勃、生龙活虎。这是连队的早晨,这一切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我多么想留在连队啊!然而,翌日上午又接到电话通知,马上带好行李,到团部结合,然后到师部开会,晚上就不回来了,在连队的帐篷里只过了一夜,这就是第一次在军队帐篷的生活。
(二)接受再教育
来到部队没有几天,为了接受对知识分子再教育,就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,我来到密云县西庄子公社。在四清工作队中,要做好刘汉文团长的医疗保健,他有高血压病,经常需要测量血压,调整用药,工作队的人员发生疾病,我也要去安排治疗。住在西庄子卫生所里,不少村民来诊所门诊,有时也给这些村民看病,对于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,真是求之不得,为病人治病是满腔热情、乐于从命的,非常幸运,在四清工作中,我还担负着医生的责任。
西庄子公社是一个山区中的小村庄,在一个小丘陵的南坡下,村子的南侧有一条小河,水深不到一米,宽约20多米,水流哗哗作响,近闻如战马嘶鸣,群众称白马关河。走出村庄,基本都是山沟小路,向西就是在一个山梁,那里有西弯子村,顺着刚修好的公路,向北可以到冯家峪村,向东到老爷岭村,向南是西庄子公社的几个生产大队,都在密云水库的北岸。村里的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,春夏秋冬,每天都是吃两餐,多以地瓜为主食,现在是1965年,绝大多村民从未见过汽车,我们四清工作队人员,要和当地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有一次和农民一起干活儿时,一位农民用绳子拴住一个男孩,干活时,就把男孩拴在树旁,我们很不理解,经过询问,这个小孩出生时就是傻子,在这个村子里,这样的小孩还有好几个。
参加四清工作队,我负责西庄子卫生所的四清工作,住在西庄子卫生所里,和卫生所的医生生活在一起,其时,幸好遇见北京医学院附属北大医院医疗队的队长林传镶教授,有一个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床,晚上,我们两个人就睡在这个床上。我在医学院读书时,有一本《内科学基础》教材,他就是这本书的主编,这次能相见,非常幸运,这是我学习医疗知识的极好机会,后来,林传镶教授告诉我,由于山区群众近亲结婚比较多,不少人家的小孩有畸形,有的是先天愚傻,村里的傻孩子多,就不奇怪了,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自言自语叹息道:真是贫穷落后啊!如此贫穷落后的农村啊!
1965年9月16日,来到这个山村才十多天,这天早晨,刚刚吃完早饭,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卫生所,找到卫生所的杨明书医生,请求给一毛钱的药,杨明书医生毫不迟疑地给她3片麻黄素,看样子,这是本村一位很熟悉的病人,未见到病人,为何就能给麻黄素药片呢?麻黄素这个药是一种限制性药品,不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的,这样的诊疗过程,我有点疑惑不解,我紧随老太太走到她家,想看个究竟,进到她家一看,她家有一位十四岁的孙女,叫郑秀兰,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气,口唇明显发紫,已经两天不进食了,家中老大爷说,小孩得病已经一个多月了,从公社信用社借了三十块钱,钱用完了,病还没有好”。我回到卫生所,询问卫生所负责人陈继儒医生,他的回答更是出乎我的意料,说得非常轻松而又明确:“这个孩子不行了,只好等死!”。难道贫穷的小孩真的没治了吗?是没有钱还是无法治的病?我立刻和医疗队的林传镶队长讨论和商量,决定再到郑秀兰家中看望病人,经过简单的听诊检查,病人两肺满布哮鸣音,可以明确诊断为,慢性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,这是一个可救治的疾病,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,寒假回家时,就曾用过针灸,给本村的病人治疗过这种病,这一次,我大胆地用针灸给郑秀兰治疗,取了四个穴位(定喘、肺俞、足三里、合谷),大约10分钟以后,哮喘渐渐减轻了,由于医疗队的大力支持,在林传镶教授的指导下,选用了支气管解痉药、抗过敏药,又用了一些消炎药,经过两天的治疗,病人已经能起床自由地行走了,肺部也听不到哮鸣音了。郑秀兰终于得救了,第一次能为山区农村的孩子治好病,我感到无比的开心。
来到西庄子公社已经一个月了,一个偶然的机会,看到卫生所所长陈继儒给一个人拿止痛药,他嘴里还叨唠着:“没有特效药,你到哪看,也只能是这样”。我有点不理解,就问了陈继儒这是怎么回事?他立刻告诉我,西庄子大队有个郭刚荣病人,患有直肠癌半个多月了,躺在家里,现在只能对症治疗,用些止痛药。带着特有的好奇心,我找到郭刚荣家,说明来意后,问了一下病情。郭刚荣告诉我,大约在二十天前,发现大便有血,并有腹痛,同时还有腹泻、发热等不适,病后十天左右。卫生所陈所长来看过,他看过大便后,很果断地说,大便这样了,全是脓和血,是直肠癌晚期啊!没办法啦,等着吧,家里没有钱,只能等着啊。我又问郭刚荣,陈所长检查过你的肛门吗?郭刚荣很相信陈所长,他说,陈所长技术高,不用检查肛门,一看大便就知道了。我还是有些疑惑,直肠癌不经检查肛门就能诊断吗?直肠癌为何发热、腹泻?有脓血大便的直肠癌病人多为晚期了,病程还不到一个月,现在看起来也没有消瘦,难以解释。我简单地检查了病人,一般情况还好,手测体温为中等度发热,心率八十二次,心肺未发现特殊,腹部检查,肝脾不大,未扪及包块,无固定压痛点,肠鸣音活跃。见到上午刚刚排出的大便,明显的脓血便,并有少量白色粘液,我回到卫生所,拿了橡皮手套,给病人做了一个直肠指检,未发现直肠有肿块,在手套上,没有血迹。这时候,我确信这个病人起码不是直肠癌,很可能是感染性肠道疾病。鉴于西庄子卫生所的具体条件,没有大便检验,没有结肠镜检查,我建议病人先用些肠道消炎药,观察病情变化,必要时,再考虑下一步检查和治疗。因为郭刚荣知道了我是北京来的军医,同意接受我的治疗方案。三天的黄连素、四环素治疗量,四天的氯霉素治疗量,病人腹痛、腹泻、发热的症状全部消失了,大便正常了。郭刚荣连自己也不敢相信,他的直肠癌好了。这个病人的治疗,也曾使我胆战心惊。没有肠镜的检查,就否定直肠癌的诊断,没有实验室检查大便,就诊断肠道感染。我这个勇敢的莽撞,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。事后,我也捏了一把汗。三十五年过去了,我也退休后,再次去西庄子村旅游,郭刚荣的儿子还记得我的名字。
1966年的1月21日是春节,这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,在春节期间,我们四清工作队队员有七天的假期,但是每个工作队需要有一个人原地留守值班。
我们工作队的其他同志,不是家在北京市,就是在北京市有亲人或朋友,为了让他们可以回家过春节,我向领导请求,我的家不在北京市,可以留守在西庄子,再则平时有很多社员要求我给他们看病,因为工作忙,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,如果留在西庄子,还可以利用这七天的时间,为西庄子的社员诊治疾病,这不是一举两得吗,我的请求得到领导的批准,我非常高兴。
我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负责西庄子公社的供销社、小学校、兽医站和西庄子卫生所四个单位的四清工作,在春节期间,供销社的生意兴隆,卫生所的医疗工作也不少,虽然学校和兽医站的事比较少,但是,也不一定完全没有事,由此可见,春节假日期间,就留我一人值班,我肩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。
1月18日,留守的第一天上午,我与西庄子卫生所所长陈继儒讨论了春节期间的值班和门诊问题,与他商量好,必要时,我可以门诊或出诊。由于供销社的门市部售货太忙了,下午我也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售货员,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,全天的销货量达到了七百多元,是平时的一倍多。晚上又和供销社的王德义主任谈了心,和他讨论了除夕下午的工作,根据当地习惯,是否可以照顾职工早点回家,就这样我愉快地度过了留守的第一天。
说起春节的除夕,我的思绪万千,前年的春节除夕,我是在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宿舍的传达室,孤独一人,静静地沉思。去年的春节除夕,我是实习医生,也没有回家,那是在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度过的,那时我为工人医院全体实习医生,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春节晚会,身心的疲劳是小事,事后的寂寞、郁闷,几乎成了春节的主题。今天的春节除夕,这是一个不平常的除夕,这是我离开医学院来到军队的第一个春节,今年穿上了黄军装,衣食无忧,安闲而又幸福地欢度春节。今天我来到北京市郊区,在长城脚下的小山村过春节,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我想到远在家中的父亲、母亲和弟妹们,他们是怎样过春节的呢?或许会比往年更好吧!
夜幕降临了,西庄子村的除夕是静悄悄的,村民的房前屋后,几乎没有人走动,西庄子村时有喧闹,远处时而传来稀稀拉拉的爆竹声,没有一家门前有红灯笼,但是,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有红红的对联或福字。
除夕的晚餐,按照惯例是吃饺子,晚饭后,我在西庄子供销社的院子里来回踱步,供销社的职工马宗武也走过来,我们边走边聊天,马宗武告诉我:“这儿的春节有很多特色,有不少乡风民俗,不要只看到屋外没有人走动,现在,每家每户都在吃饺子、喝酒呢。喝酒是山村农民的一个习俗,女儿春节回娘家,总是要带一瓶二锅头。除夕的早餐吃合乐,合乐是专用工具压出来的面条,或叫饸饹,饸饹是一种油炸的面食,合乐和饸饹,其谐音皆表示合家欢乐。除夕的晚上要吃饺子,北京人有句顺口溜:好吃不如饺子,再穷的人家,春节总得吃一顿饺子,没有面粉,白薯面也可以,还有一个小小的笑话,有人故意将饺子包得松一些,在煮饺子时,当饺子破了,不能叫破了,而是应该立刻说挣了,其意就是挣到钱了,还有人故意在饺子里包进去一个硬币,谁吃到这个带硬币的饺子,就是今年要发财了。除夕的晚上要多做一点饺子,留一些在大年初一吃,表示年年有余粮。这里的乡风村俗可能还有很多,就这些新闻,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。正想回屋里取暖时,供销社王德义主任和张凤勤职工邀请我和马宗武在一起打扑克,房间里点着煤油灯,收音机播放着中央广播乐团春节演唱会的乐曲,在这山区的角落里,竟然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欢乐天地,我也贵为一尊。当今国家,当今农村,仍在困难时期,我实感汗颜有愧!快到夜里十二点了,也谈不上是守岁,大家就收场了,回到西庄子诊所宿舍里,稀里糊涂就睡着了,一阵一阵爆竹声,把我惊醒了,天亮了,春天来了!
大年初二,黄峪口大队有多个发热病人,几个村民来卫生所请医生出诊,我立刻和卫生所负责人陈继儒说,值班的医生不能离开岗位,我去出诊吧。他同意了,并交待出诊的路线,我背上出诊包,向西经过西弯子大队要翻过一个小山,这里基本上都是山路,不能骑自行车,大约步行了五里多路就走了一个多小时。黄峪口大队有三十多户人家,全住在一个山沟里。山沟入口处,一位大妈把我接了回去,他的女儿冯亚兰正在发热,我检查病人时,发现有右上腹胆囊区的触痛、压痛的体征,我诊断她的病是急性胆囊炎,给了她退烧药和消炎药。顺着山沟向前走,挨家挨户巡诊,有十多家均有发热病人,其症状大都相似,发热、咽痛、鼻堵、流涕,基本上是感冒,很可能是一次流行性感冒,我都分别给了相应的药物治疗。有一户人家,只有两位老人,看相貌皆为近六十岁,两人均发热,也是感冒,但是,没有钱拿药,他们的退烧药和抗感冒药,仅仅是五元钱,我替他们付了药费,并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方法,用少许生姜和大葱白加入两碗水中,水烧开三分钟,待水温后,饮服,一天服两次。回到诊所后,向诊所交完了医药费,太阳已经下山了,早春的大地有明显的寒意,我的心里热乎乎的。

从春节的第三天开始 ,我就分别到西庄子公社的董各庄、杨各庄、老爷庙、赶河厂、高家岭、前宝峪岭等生产大队巡诊。每个生产大队的社员都十分热情,上午看完病人后,抢着留我吃饭,我都一一谢绝了,我身上带的几个地瓜是最好的午餐。在赶河厂生产大队遇到的一个病人,引发了我的深思。病人是一个酷爱抽烟的老年人,六十来岁,男性,每到冬季,总是咳嗽、咳痰,时好时坏,已经五年多了,久治不愈,要求我再给他看看。我给他检查了身体,除肺部听到干罗音和少量的湿罗音,其他基本正常。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给他用了些消炎药、止咳、化痰药,并建议他停止抽烟一周,结果五天后,他特意到西庄子卫生所来感谢我,并喜气洋洋地告诉我,多年的咳喘病好了。
在西庄子公社将近一年的时间,与其说是四清工作队的队员,还不如说是西庄子公社卫生所的“客座医生”,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医生,能为北京郊区的山沟里农民治病,真正感受到山沟里的农民太需要医生了,我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,的确是受到了再教育。
(未完待续)
整理:吉 农
编辑:乐在其中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