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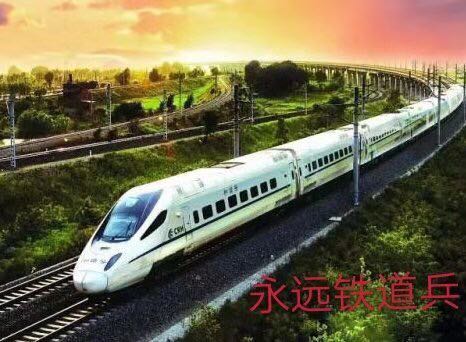
仪陇:朱德与母亲陈列室
朱德人生中第一位老师,是他的母亲——钟氏。
钟氏是一位奇女子,出身贫寒的流动艺人家庭,早早地就嫁了人,成了仪陇马鞍场朱家老二朱世林的媳妇儿。
朱家祖籍是广东韶关,明末清初时举家搬迁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四川,成了“客籍”人。
连年战乱的四川人烟稀薄,常驻于此的人霸田占地,当上了土财主、地主,有钱有权,嚣张跋扈。
身为外乡人的朱家,想要在当地站稳脚跟,难如登天。
一来,一家老小都没怎么念过书,文化水平不高,无法靠脑子赚钱;
二来,他们并无傍身的手艺,也没办法从事轻松的工作;
三来,摸摸钱袋,空空如也。
能怎么办,只好租种地主的几亩地,为地主当牛做马,把收成的粮食卖了,换取生活费。
朱家是一个大家庭,里里外外十几口人,长幼、叔伯、妯娌都生活在一起。
钟氏没来之前,朱家的男子是主要劳动力,钟氏嫁过来之后,因身材高大结实,成了家中的顶梁柱。
虽说,钟氏原本家境就不好,可刚嫁过来时,脸蛋红扑扑的,两双手也白嫩地能掐出水来,这很符合一个二十岁姑娘的相貌特征。
生活压垮了她,不下十年的时间里,她的脸因在太阳底下暴晒而变得黝黑,纤纤玉手变得粗糙,粗粗的血管清晰可见。
从前她披着头发,后来她为了劳动方便,把头发盘到后颈,挽成一个发髻,平添了几分贤惠。
朱家没有自己的房屋,祖孙三代挤在地主丁邱川废弃的一幢破仓屋里,光线比较昏暗。
这样的环境没有吓跑钟氏,她心甘情愿为整个家付出全部心血,没日没夜的操劳着。
每天,天还未亮,她就已经从床上爬起,先是到厨房做好全家人要吃的早饭,紧接着到地里干活,把种田、种菜、挑粪的事情都给做完,忙完了再回去。
到了晚上,她坐在煤油灯下纺线,灯时而亮时而暗,偶尔人过去带来一阵风,还得抖上三抖,很费眼睛。
等到一家人都就寝了,钟氏才会放下手上的活计,钻进被子睡觉。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钟氏,其实“起得比鸡早,睡得比狗晚”很贴切。
早年间,朱家的生活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,钟氏凭借一己之力,稍稍改善了家中条件,让大家不至于沦落到去街上乞讨。
除了养家糊口,钟氏还为朱世林孕育过13个孩子,但由于家里太穷,只留下了6个男孩和2个女孩,其他五个没能养大。
朱德是钟氏的第四个孩子,也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。
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, 二哥代凤比他大两岁,姐姐15岁时就出嫁了。
他出生时,钟氏已经28岁。
父母按照“代”字辈,给朱德取名为代珍。
俗语有言:幼年学的,像石头上刻的,朱德在钟氏的身上学到了很多,包括了勤劳俭朴的好习惯。
在他成长的过程中,钟氏早出晚归,操持内外,他和兄弟姊妹身上穿着的衣服,是钟氏一个一个夜晚费心织出来的。
先织布,再拿去染色,由于织的足够厚,和铜板的厚度差不多,耐穿,往往是老大穿过, 老二、老三接着穿。
朱家吃的比较穷酸,早上吃高粱稀饭,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,配菜是青菜,一般只有一碗。
午饭和晚饭,以掺有豌豆、蔬菜、红薯的杂粮饭为主。
肉是少有的,逢年过节才可能吃得上,碰到了不丰收的年月,一顿都没。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朱德五岁起就开始上山打柴、割草,换作是现在的孩子,大概率是不愿意的,即使愿意,可能也需要获取一些“劳务费”,简称用钱买乖。
朱德不这样,他太知道钟氏的辛苦了。
一个女子怎会不爱打扮,不爱涂抹胭脂水粉,不爱穿漂亮衣服?
钟氏心里头可能有过如此的梦想,可最终被生儿育女所累。
朱德未满十岁,钟氏便未满四十,可在朱德的记忆里,那个时候,钟氏就已经苍老憔悴了。
不是岁月不肯放过她,是繁重的劳动,缺衣少食的日子不肯放过她。
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,空洞的眼眶里,一双褐色的眼睛充满忧愁,再加上逐渐花白的头发,打满了补丁的裤子和短褂,她和整个乡村融合在了一起。
旧中国的女性,骨子里的三从四德很深,钟氏没有嫌弃过朱世林,即使他没一技之长,还爱抽烟喝酒,脾气也不好,不会疼老婆。
朱德从小怕生父,可对生母钟氏,只有绵长的爱意、敬意与深深的亏欠之情。
钟氏大字不识几个,可性子温顺,还十分明事理,支持朱德摆脱泥腿子的身份,多读书,考取功名。
20岁的时候,朱德考中秀才,逐渐闻名于乡里,成了县长的座上宾。
但朱德的志向并非在小小的乡村,他在母亲的际遇里,看到了全中国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,看到了压在老百姓们头上的三座大山——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。
他想走出去,其实多多少少受到了母亲的影响。
他回忆,小时候,钟氏没办法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。
为了兼顾,她只好把孩子们都抱到菜园子里,她在一旁刨土,孩子们满园子地爬来爬去。
这个画面,读来让人胸口发闷,这得是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了。
更离谱的是,朱德出生时,钟氏正在烧饭,还没等把饭烧好,朱德就呱呱落地了。生下朱德后,钟氏立刻起身,接着做饭。
朱德放弃了在家乡发展的大好前景,打算到外头闯一闯,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人,并没有规劝朱德一定要留下来,而是一如既往地相信他的选择。
起初,朱德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,后受到了蔡锷重用,开启了自己的军事生涯。
他得空的时候,会写信给钟氏,告知自己的近况。
到了后来,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失败,共产党人收敛锋芒,转到地下工作。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,由于国民党的封锁,他一连十年未能修书回乡,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后,才得以与亲友恢复书信往来。
对此,钟氏表示体谅。
她还是做着分内的事,不辍劳作,自食其力,不希冀做了大官的儿子,能给家里什么帮助。
她不要钱,只希望肩负民族重担的朱德,能够在她身故之前,回乡见她一面。
可惜的是,自古忠孝不能两全,烽火狼烟一燃就是二十几年,朱德脱不开身,人民需要他,军队需要他。
为了大家,他只能舍弃小家。
1944年2月15日,劳累一生的钟氏寿终,享年86岁。
噩耗传至延安,已过去一月有余。
老家的信里尽量将事情写的轻松,说老太太走得很安详,没有痛苦。
朱德不想影响战士们训练,表面上云淡风轻,私底下却背负了巨大的悲痛。
他很重感情。
他的前妻伍若兰牺牲于赣州城内,他一度沉默寡言,脸上难见到笑容。
那段时间,红四军的战士也被这种压抑的气氛感染,各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提不起精神来。
这次,朱德吸取了教训,不敢在众人面前表露出难过。
可每每一人独坐于炕头时,他总要靠香烟排遣心中的愁云。
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处,他默默流泪,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,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妻子康克清说:
“这一生中如果我有什么遗憾的话,最大的遗憾,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,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。”
没有尽到孝心,让母亲钟氏受了苦,成了朱德的心结。
他发表悼文《回忆我的母亲》,感谢钟氏给了他强健的体魄,感谢钟氏教给他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,感谢钟氏鼓励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只此一篇文章,让广大群众了解到了这样一位伟大而又平凡的母亲。
无形间,钟氏教给了朱德一生都受益不尽的优良品行。
这种品行,融进了朱德的家风之中,往下传承。
他告诫子孙,要正道而行,有规矩意识,更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勤俭持家,不要有特殊思想。
他尝到了读书带来的好处,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努力学习。
但他不管做了多大的官,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农民。
他的穿衣戴帽,他的思维方式,他的生活起居,无不保留着农民式的风格,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。
他的母亲钟氏,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,而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,所以,朱德以自己是一位农民而感到自豪。

美篇链接:点击查看
编辑:舒冉

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
版权所有©2019
京ICP备1204503号